李白赞美仙人掌茶,陆龟蒙自种顾渚山茶,唐代文人推动中国茶文化发展

有唐一代,饮茶之风大盛,上至王公贵族,下至闾里细民,已经将茶视为生活中的必需品,甚至达到了“闾阎村落皆吃之。累日不食犹得,不得一日无茶也”的程度。而将大唐的这种“比屋之饮”,提升成为一种文化,离不开文人们的努力。一个陆羽,一个卢仝,以他们的实践和对茶的理解,让唐人的饮茶具备了深厚的文化意味,而骨子里本身就是文人的他们,更为文人茶的蔚然成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事实上,茶与诗在文风灿然的唐代,更像一对不可分割的双生子,当诗歌在淡淡的茶香中氤氲成一缕清醇,当茶盏中升腾起隽永淡雅的文字,诗歌便更加清丽超俗,茶也便融入了更深的文化内涵。行走在大唐的文人们,不论身居庙堂也好,散处江湖也罢,在茶香四溢的大唐,都在寻找着茶与诗最佳的契合点。遍览《全唐诗》,我们可以看到的茶诗达数百首之多,这些茶诗题材多样,涉及到茶的栽、采、制、煎、饮,以及茶具、茶功、茶德等方方面面,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茶诗背后,正是大唐文人们如茶一般的生命意趣。
常闻玉泉山,山洞多乳窟。仙鼠如白鸦,倒悬清溪月。
茗生此中石,玉泉流不歇。根柯洒芳津,采服润肌骨。
丛老卷绿叶,枝枝相接连。曝成仙人掌,似拍洪崖肩。
举世未见之,其名定谁传。宗英乃禅伯,投赠有佳篇。
清镜烛无盐,顾惭西子妍。朝坐有馀兴,长吟播诸天。
———李白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》
李白的这首茶诗,是中国关于仙人掌茶的最早记录,在此诗之前,有一小序,说是李白在金陵遇到了恰好云游至此的自己的族侄——中孚禅师,他向李白展示了数十片采自荆州玉泉山的茶叶,此茶“拳然重叠,其状如手,号为仙人掌茶”,因其所生之地近“清溪诸山,山洞往往有乳窟,窟中多玉泉交流”,故生长于斯的这种仙人掌茶“清香滑熟,异于他者”,“能还童、振枯、扶人寿也。”生就一副仙风道骨的李白从来就是在山水的陶养中且行且吟的歌者,而偏偏茶尤其是好茶的生存环境又是深山幽谷云雾缭绕之处,向往林泉的李白当然要倾尽笔墨,表达自己对这片灵动的树叶的喜爱。而如果说盛唐文人对茶的理解还仅仅在与其自身意趣形成对应,那么进入中唐,随着陆羽《茶经》的风行于世,随着越来越多的野生茶树被引种成功,文人们对茶的领悟已经有了更多可以依托的载体。“紫芽连白蕊,初向岭头生。自看家人摘,寻常触露行”,这是张籍眼中郁郁葱葱的茶岭;“闲来松间坐,看煮松上雪。时于浪花里,并下蓝英末 ”, 这是陆龟蒙的林间之趣;“石窗紫藓墙,此世此清凉。研露题诗洁,消冰煮茗香”,这是姚合为我们在唐诗中留下的唯一消冰煮茶的记录……显然,沉浸在漫漫茶香中的大唐文人们,已经将中国文人心中普遍存在寄志名山幽隐林泉的文化心理,融入了茶——这片葱翠淡雅的中国树叶,并在清冽的山泉水中,沏泡出沁人心脾的清香。

茶
香叶,嫩芽。
慕诗客,爱僧家。
碾雕白玉,罗织红纱。
铫煎黄蕊色,碗转麹尘花。
夜后邀陪明月,晨前命对朝霞。
洗尽古今人不倦,将知醉后岂堪夸。
——元稹《茶》
在《全唐诗》中行走,元稹这首有趣的茶诗让人眼前一亮,以宝塔的形式来排列诗歌,在唐人诗歌中非常少见,而诗情横溢的才子元稹采取这种创作形式,与其说是他对茶献上的一份特别的钟情之作,不如说是茶的自然之趣冲开了元稹的文人意趣,让元稹得以在高手云集的《全唐诗》中淋漓尽致地耍了一把俏皮。其实,元稹的状态又何尝不是唐代文人茶的状态呢?正是悠远的茶香,让大唐文人可以暂时放下求取功名之累,仕途奔波之苦,籍着一盏清茶,进入物我两忘之境,而一旦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,文人间的乐趣便如清冽的山泉水一样汩汩而出,喷涌不绝。在茂林修竹之间,文人常常会以茶点会友,称为“茶会”、“茶宴”或“汤社”,当一壶香茗沏泡开来,文人便观其形,察其色,闻其香,品其味,以眼韵、鼻韵、喉韵、神韵的共同作用,感悟茶叶之妙,而三杯过后,木瓜、元李、杨梅这些干些果品便会摆上案头,为与会者漾溢着茶香的味蕾增添一丝别样的滋味。当然,除了文人们以诗茶自娱,唐朝政府也喜欢举办一些茶宴茶会,并延邀一些社会名流文人士子们入席,在这些官办的茶会中,尤以顾渚山茶宴最为盛大,由于顾渚山地处湖州常州交界,又以贡茶紫笋茶和阳羡茶闻名遐迩,因此每到早春造茶,两州太守都会联合举行盛大的茶宴,这场茶宴又被称作“境会”,其中自然少不了文人们的赋诗助兴。据说有一年正逢“境会”,彼时正在任苏州剌史的白居易本应前往,却不慎因骑马摔伤,无法参加,遂以一首诗向两州太守表达遗憾,“青娥递舞应争妙,紫笋齐尝各斗新。自叹花时北窗下,蒲黄酒对病眠人”,没能参加成“境会”的白居易,已然在心中感受到了这场茶宴的盛况。

平生无所好,见此心依然。如获终老地,忽乎不知还。
架岩结茅宇,斫壑开茶园。何以洗我耳,屋头飞落泉。
何以净我眼,砌下生白莲。左手携一壶,右手挈五弦。
傲然意自足,箕踞于其间。兴酣仰天歌,歌中聊寄言。
—— 白居易《香炉峰下新置草堂,即事咏怀,题于石上》
大唐文人们就是这样,他们总能从看似简单的事物中生发出别样的美来,当茶文化的勃兴激发了文人茶的更深层次的审美追求,那么文人茶的贴地而行,则让茶文化的意蕴得到进一步的放大与舒张,白居易在香炉峰写就的这首茶诗,正是这种逻辑关系的生动演绎。“如获终老地,忽乎不知还。架岩结茅宇,斫壑开茶园。”曾经因为没能参加顾渚山茶宴而懊恼的白居易,不仅对酒情有独钟,对茶更是达到了酷爱的程度,早上起来,他要从一杯茶开始自己的一天,每餐过后,他要用茶冲涤口中的油腻,至于写诗作文,更是须臾不可缺茶,他曾大赞用渭河之水煎出的“满瓯似乳”的蜀茶,也曾自云琴与茶是其“穷通行止长相伴”的爱物。不仅如此,他还要亲身感受种茶、研茶之乐,当一座傍山而起的茶园在他的耕耘下一片葱笼,这位高产的大唐诗人便收获了另一份来自山野的馈赠与满足。而同样有此爱好的,还有陆龟蒙,这位被称为“天随子”的晚唐诗人,常常将自己比作涪翁、渔父、江上丈人这些江湖隐士,不仅如此,他还亲自身扛畚箕,手执铁锸,在顾渚山下开垦出数百亩茶园,每有闲暇,陆龟蒙常常会便带着书籍、笔墨和一把茶壶,静坐于茶园之中,享受与自然的融融之乐。
是的,正是大唐文人的身体力行,为唐代茶文化的弘扬与发展、发醇与提纯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内驱动力!

本头条号"唐诗宋词有风云”已签约维权骑士,严禁盗用,违者必究;图片源自网络,侵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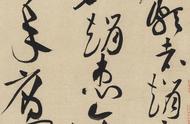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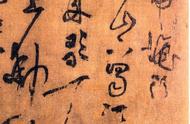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80号
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80号